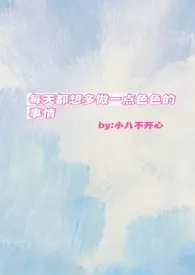「商佐有没有和姐姐提过这件事?」
「没有,他不会跟我说这些。」
「啊,好害羞。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做这种事⋯⋯姐姐妳说他会不会觉得我是随便的女生?但我真的觉得我可以等他。」
司倪觉得此刻应该附和才不至于让场面尴尬,她听过太多客人的感情事,胡亭葳的只是其中一条。
室内环绕着爵士音乐,胡亭葳仍旧淘淘不绝,希望她给她一点建议,或者安慰。面具下的司倪是擅长——成为旁观者去安慰别人。
她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让胡亭葳对他改观。
譬如商佐其实并不如外人所见的那般热情,在家多半少话,思想也并非无时无刻都处于正向,偶尔还有点悲观。他好胜心也强,嘴上不说,却为了一场比赛不眠不休的练习。
他也爱面子,在朋友面前让他难堪是绝对不允许的。
「不会的,商佐不是那种人。」
胡亭葳双手合十。「有姐姐这些话我就放心了。」
后续内容已被隐藏,请升级VIP会员后继续阅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