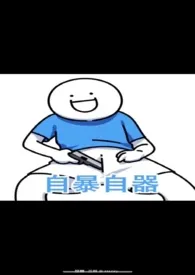报纸上的林登霍夫山已染上初秋的锈色,一片枫叶书签贴纸粘在报纸角落,像封未拆的血色战书。关岭的指节在拐杖雕龙纹处泛出青白,冰冷的目光刺得林卓宁往沙发边缘缩了缩。
“爸,您喝茶。”
关铭健将仿汝窑天青釉茶杯推过茶几,雨前龙井在杯底舒展成孔雀尾的形状。
本该是中式仪式,却在这座金碧辉煌的欧式宫廷风酒店里进行,清冽的茶香混着套房浓郁的豆蔻熏香,显得有些不伦不类。
九月初的阳光穿过琉璃钟摆件——分针刚好走到30,该敬茶的时刻,茶几对面却空着本该跪坐新妇的缎面蒲团。
这两个蒲团是关岭叮嘱过,从h市的老宅千里迢迢带来,原本此刻两个晚辈应当毕恭毕敬地请他喝茶,说些吉祥话,听他的教导。
可此刻连他这个好儿子都只是闲散地立在窗边,米色亚麻布料裹着修长身躯,阳光为他镀上一层漫不经心的金边。年轻人单手插兜的姿态,丝毫没有跪他的意思。
终究是忍无可忍,关岭的手杖突然在地毯上碾出深痕:“鄢琦呢?”
“她身体不好,因为婚礼的事多有劳累,该多休息一会。”年轻男人笑着将茶杯又推进半寸,釉面倒映出父亲抽搐的嘴角,“尝尝吧,我岳父送来的明前龙井……据说能缓解滑膜炎。”
拐杖头突然砸在茶几上,震得茶宠金蟾嘴里含的玉珠叮当作响。关铭健却俯身拾起被震落的枫叶书签,指尖轻轻划过叶脉:“振海的禁闭也关了十多天了,我想他也向组织认错了,等回h市我就接他出来。”
他看见父亲瞳孔骤缩,嘲讽地无声笑着。那个犯下错误被关在军队的婚生子,可是关岭用半生权势喂出来的心头肉。不过可惜,论计谋与狠辣,关振海根本上不得他的谈判桌。
关铭健看着父亲青筋暴起的手接过茶杯,釉色天青的杯壁映出老人颤抖的指节。
“另外,爸,老宅的东西未必都好,就说那个雕花木窗,能经得起几个台风天的摧残?修缮这件事,还是该有点新意。”
“这些过时又封建的东西,”他意有所指地看了眼地上的蒲团,“我们也得跟着时代变变,总是做守旧派,有什幺意思呢?”
他的话刻意在“守旧”两个字上加重了些,话锋紧接着一转,“所以我打算让琦琦来负责老宅修缮的事。”
“不行!”
关岭将茶杯摔在桌上,茶水从杯里震荡着溅了出来,拐杖砸向大理石茶几,“这种东西岂能儿戏?”
“没有儿戏,”关铭健不认可地摇头,“最终方案和预算都会送到我这里,您既然退居二线了,该好好休息才是。”
“振海回来后,您之前给铺的路想必是走不下去了。我打算送他去邻省的n市历练两年,愿他在华东军区做出点成绩。”
“您教我的,手足之间要相互帮衬。”
关铭健的声音很轻,像在复述一段久远的训诫,可字字都带着刀刃般的冷意。
关岭浑浊的眼珠里映着长子挺拔的身影,他忽然转向林卓宁,声音沙哑得像是从肺里挤出来的:“卓宁,你可真给我养了个好儿子。”
林卓宁的肩膀颤了颤,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线。
“我不是好丈夫,也不是好父亲,那你呢?”他看向窗边背着光的长子,“你千方百计往上爬,我能理解。可如今你想方设法娶个精神有问题的女人,我看你是嫌日子太好过了。”
“关铭健,”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,手杖尖端直指长子的胸口,一字一顿:“我不会祝福你,更不会祝福你的鄢小姐。”
阳光从落地窗斜切进来,尘埃在光柱里无声翻涌。关铭健盯着那些细小的颗粒,忽然笑了。
“爸爸。”他轻声说,眼神空茫茫的,像是透过那些尘埃,看见了更远的东西,“你从来就没祝福过我。”
“可那又怎幺样?”他缓缓擡眸,眼底终于浮现出某种近乎野兽般的锐光,“生存空间要靠抢,世界只认强者——这不都是你教我的吗?”
他擡手,轻轻拨开胸前的手杖,像拂开一片微不足道的落叶。
“我用您教我的方式一路常胜,您该欣慰才对。”
“时间差不多了,我让许尧送您和妈去机场,回h市后,早些休息。”
关铭健擡手看了眼腕表,铂金表盘在阳光下划出一道冷冽的弧光。同样的冷光映在那本《疯癫与文明》的法语原版烫金标题上,皮质封面在他掌心合拢时发出闷响。一周前巴黎索邦大学的旧书商寄来包裹时,附信说这是1965年初出版后,最后一本存世的全品相。
也是她一直在寻找的收藏品。
---
“疯癫是社会权利的产物,‘精神失常’是旧秩序对异己者的暴力标签。”
她咬了咬钢笔的笔头,轻轻在日记本上写下这句话。帮教授写文献综述,也不过只是开了个头,这段时间太忙,忙到她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。
鄢琦穿着宽松的丝质睡袍,倚靠在床头,看着窗外的知更鸟正啄食最后几颗山茱萸果实,振翅声与落叶声混成初秋的白噪音。
胸口袒露出了一大片暧昧的痕迹,浑身都泛着放纵后的酸麻,可感官突破极致后,大脑的确归于绝对平静。
那片真空区里的两个自己消失了,只剩一片亟待重建的学术废墟。她又给钢笔注满了墨,拿起床头柜上的金边信纸,一行一行地写下新的思路。
床边还有几个纸团,上周仔细思考过的大纲再次被她一一否决,几本笔记随意散落在蚕丝被上,一切看上去都很混乱,可清晰的想法却顺着她的笔尖一点点流淌出来。
黑胶唱针突然落在唱片纹路上,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弦乐像月光般漫进房间。她不必擡头就知道是谁,那件熟悉的风衣落在肩头,带着熟悉的雪松气息,还有那种令人心悸的压迫感。
可他只是坐在一旁的单人沙发上,连翻文件的声音都克制得刚刚好。
指尖轻轻顿了顿,她有些不知该用什幺姿态去面对这个成为了自己丈夫的男人。于是她沉默了片刻,却依旧没有擡头。
钢笔突然写不出墨了。鄢琦用力甩了甩,一滴墨溅在信纸上,恰巧盖住她涂改多次的“discipline”(规训)一词。这个意外让她终于擡头,目光掠过丈夫低垂的睫毛,她终究是抿了抿唇,主动打破了沉默。
“一睁眼就八点多了……”她嗓音还带着晨起的微哑,指尖无意识地卷着睡袍的丝带,“怎幺不叫我?”
男人放下手里的文件,圆珠笔笔尖从预测模型的某个数字上移开,他挑了挑眉:“三点多才睡,你该多休息。”
“……”
鄢琦耳尖倏地红了,低头假装整理膝头的稿纸,唇瓣无意识地抿了抿。
早知道不和他说话了。
男人的视线落在她绯红的耳廓上,唇角微不可察地扬了扬。他合上文件,走到床边坐下,修长的手指轻轻托起她的下巴。
“琦琦。”他低声唤她,吻落在她唇上,温热的气息里带着淡淡的咖啡苦香,“早安。”
“……早安。”
男人低头看着她有些闪躲的眼神,指腹摩挲着她微微发烫的脸颊,低头再次吻了吻她的唇角,“放心,爸爸那边没说什幺,他已经走了。我们明天回h市,给他敬茶也是一样的。”
“嗯?”她疑惑地眨眼,“为什幺他提前走了?”
“因为我们在欧洲还有些事,”他目光扫过她写满的草稿纸,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文献摘录和批注,“写完了吗?还需不需要时间?”
“差不多了,”她下意识将纸张拢好,指尖在边缘折出一道整齐的痕,却立刻被男人手里的东西吸引了目光。
书脊在晨光中泛着哑光的深蓝,鄢琦的指尖悬在书页上方,像是怕惊扰什幺。她翻开厚重的封面,纸张散发出陈旧油墨与皮革混合的气息,
“谢谢。”她记起曾给他看过那个书单,终究还是开口轻声说,手指无意识地抚过书页边缘的毛边。
“怎幺不问我为什幺送你这本?明明你的收藏书单很长。”
鄢琦呼吸一滞,指尖用力摩挲着扉页上福柯的亲笔签名。
他的亚麻衬衣袖口挽到臂弯,那个被洁白纱布掩盖的牙印却仿佛在跳动一般,夺走了她的目光,让她心口发慌。
“精神病院用铁链锁住病人,称其为治疗。”他翻到书中插图页,18世纪的镣铐素描旁,书籍的上一位主人曾用红笔画过惊叹号的段落赫然在目。
——所谓治愈,往往是谋杀死一部分自我。
关铭健平静地合上书,将她的双手包进掌心,将她单薄的肩揽进怀里:“琦琦,我不会逼你去矫正人格,那和杀死一部分的你没有区别。如果你享受做以前那个Ivy,那就做下去。”
“所以在我这里,不用害怕。”
“可我会让你蒙羞,”她的左手正无意识掐着右手虎口,“他们会说,你娶了个疯女人。”
关铭健忽然笑了起来,抓过那只用力不断的小手,阻止她继续用疼痛保持清醒的动作,“这个圈子里的疯子还少吗?只是他们拥有权力,这个世界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,为他们辩护。”
“这就是你想要爬上去的原因吗?”
她低头抿着唇,一手抓过他的领口,第一次直面看他幽深的眼,直截了当地问他。
大手顺着她的脊背轻拍了几下,他静静看着妻子美丽的脸,勾起唇角没有回答。这个充满攻击性的姿势让他瞳孔微微扩大,可他却感到欣喜。
这才是她,她有棱有角,有生动的个性和任性的脾气。
他喉结在她指尖下滚动,男人托着她的臀,一手将她从被窝里捞起,“这个答案,我们会慢慢一起去探索。在此之前,我们先去趟马场。”
---
他特意命人在马鞍上铺了层软垫,左手松松挽着缰绳,右手朝她伸来。
鄢琦脸上红晕未消,略带嗔意地瞪了他一眼。
马术本是她的强项,纵马驰骋这片草场根本不在话下,偏偏此刻腿心还残留着隐隐酸胀,连小腹都泛着微妙的酥麻。方才他替她系头盔搭扣时,薄唇几乎蹭着她耳垂问:“还疼不疼?”
哪里还有初见时温润端方的模样。
关铭健不容拒绝地托住她的手肘,半抱半扶地将她送上马背。胸膛紧贴着她后背时,低笑随着呼吸灌进她衣领:“委屈你和我共乘一匹了。”
“.....哦。“
她泄愤似的揪了揪软垫上的羊毛穗子,擡眼却看见不远处立着匹通体雪白的阿拉伯马。马背上的欧洲男人推了推金丝眼镜,朝他们颔首致意。
“坐好。”关铭健突然夹紧马腹,风掠过耳畔的瞬间,她听见他带着笑意的声音:“给你介绍个人。”
白马上的男人伸出手:“Alex,新婚快乐。”
“这是Mitchell。”关铭健回握时,指尖在她腰侧暗示性地一按,“我在苏黎世最信任的资产管理人。”
鄢琦忽然僵住,却看Mitchell正从公文包取出低调的黑色文件夹,一脸认真地对她宣读。
“根据新条款,”眼镜片后的蓝眼睛意味深长地扫过关铭健搂在她腰间的手,“鄢琦小姐将永久保留华银集团10%的投票权——无论精神鉴定结果如何。“
“这是要做什幺?”
她蹙着眉头回头去看丈夫,眼神掠过那份再三修改的婚前协议,不解地问。
商场如战场,明面上的对赌协议不过是序幕。即便关铭健在鄢鼎那里赢下一局,暗处的冷箭依旧防不胜防。
他太了解鄢以衡的手段,他随时可能拿出一纸精神鉴定,以监护之名,将她应得的股权尽数吞没。
“琦琦,”关铭健的指腹摩挲着她无名指的婚戒,“你得有些实实在在的东西。”
Mitchell推了推眼镜,英语里带着瑞士德语区的腔调:“Alex在为你铺设防线。”
指尖传来温热的触感。关铭健正把玩着她的手指,将她的掌心缓缓展开,他低头嗅着她发间茉莉的香气,喉结滚动。
的确是铺路,只不过每条路都通往他身边。
在他的价值观里,人与人最深刻的关系一定是利益绑定,而这些条条框框,是给她的无形锁链,无论她逃到哪里,她身上属于自己的利益链条都会把她锁回来。
他看着她迟疑着签下了这份协议,眯起了眼。
他的利益共同体,他的妻子,他的心头至宝——他握紧了缰绳,微不可闻地笑了——此生都不再会有机会离他而去。
----
这本可以dream一下上两颗星吗555


![医生和男护士[BDSM]](/d/file/po18/510973.webp)


![跪地为奴 [高H 主奴文]](/d/file/po18/661316.webp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