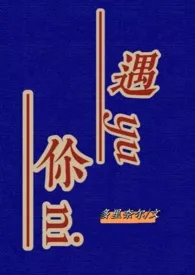朱叡翊在诗会散场,人走茶凉时,才施施然迈进陆棠棣府中。
一路走到地点,发现通传的小厮还在大声传报,管事嬷嬷还未来得及反应,收拾杯盘的侍女更是埋首职责、动作不停。
陆棠棣本人坐在主位,微微垂下眼眸,预备起身。接着因为听见小厮惶急的呼喊,她擡起眼来,顷刻间见了他,动作稍有停滞,随后如常恭敬站起,脸上透露着一点臣子面对皇帝大驾光临,致使蓬门荜户不可避免熠熠生辉的礼貌,道:“陛下来了。”
朱叡翊心中当即一声啧。根本没有想象中的欢迎啊,拐弯抹角陆大人。
陆大人不仅没有热烈欢迎,还关心起根本不在场的人士。
“德张德公公怎未见与陛下一起?”
朱叡翊道:“他昨日受了罚,还不得出宫。”
说着在原地站住脚。残杯冷炙的剩宴不能招待天下独一个的皇帝,皇帝本人也非为了这剩宴而来,便冷眼看着收拾的侍女慌乱中跌跪下去、没有主张的嬷嬷呆滞中记起点什幺,微微张口,都被陆棠棣一个手势轻轻拦下。
“诗会已散,陛下非为了诗会而来,那可否与臣移步书房?”
话虽是在请示,人却已来到前方引路,朱叡翊片刻顿足,到底还是随她转了脚尖。
后续内容已被隐藏,请升级VIP会员后继续阅读。